|
案例简述 2011年2月17日,温州市电影发行有限公司(乙方)与瑞安市文化新闻广电局(甲方)签订了《瑞安市电影城经营权出让合同》,约定:经营权出让期限为17年,自2011年12月1日至2028年12月1日止;出让金性质为电影城有偿使用费;成交价为1.2亿元,分17年支付等内容。上述合同签订后,温州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成立了项目公司,即冠旭公司,代为履行《瑞安市电影城经营权出让合同》。为此,温州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与瑞安市文化新闻广电局及冠旭公司三方,于2012年5月17日签订了《〈瑞安市电影城经营权出让合同〉补充协议》,将《瑞安市电影城经营权出让合同》乙方主体变更为冠旭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冠旭公司多次逾期支付出让金、违约金。2016年3月底,经瑞安市人民政府批准,文广旅体局将冠旭公司应于每年度11月1日前缴纳的经营权出让金改为按月度分期缴纳。经文广旅体局催讨,冠旭公司已经付清了2015年11月1日前的出让金,但应于2016年11月1日前支付的出让金227.5万元、应分别于2017年11月1日前和2018年11月1日前支付的出让金各675万元,共计1577.5万元,至今未付。违约金亦未支付。2019年1月,因政府机构改革,瑞安市文化新闻广电局被撤并,部分职能(包括对电影城实体的管理职能)归入文广旅体局。文广旅体局起诉请求判令冠旭公司支付经营权出让金15775000元及违约金。 合同变更或情势变更问题为本案争议焦点之一。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不宜对合同进行变更或情势变更,理由如下:(一)法律上不允许对合同变更或情势变更。《瑞安市电影城经营权出让合同》是通过招标投标的程序订立的,并非是自由协商订立的,因此,应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十六条的约束,通过招投标,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冠旭公司要求变更合同,其实质是要求降低电影城经营权出让金,属于《瑞安市电影城经营权出让合同》的实质性内容。变更(降低)经营权出让金的协议,是背离《瑞安市电影城经营权出让合同》的实质性内容的协议。(二)对本案合同进行变更或情势变更可能产生负面的社会效果。所谓负面的社会效果,是指可能存以较高的标价中标而订立合同;在后续的履行合同过程再以各种理由变更标价;最终以较低的实际价格履行合同。这样的操作可以绕开甚至架空招标投标程序,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三)变更合同或者情势变更的条件不具备。理由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的规定,情势变更所要求的重大变化,至少应当具有两方面的属性,即无法预见的和不属于商业风险的。但是,从《估价报告》的具体数据看,电影城场地租价即使参照综合办公楼的市场租价,其变动也是平稳的,未发生足以导致应当适用情势变更所要求的无法预见的变化。设立冠旭公司的温州市电影发行有限公司通过竞价,最终以2.4倍的溢价,即1.2亿元中标。由此产生的风险是商业风险。适用情势变更的条件不成就。最终法院判决冠旭公司偿付文广旅体局出让金1577.5万元及违约金。 法律分析 在实践中,尤其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一系列的法律现象、法律纠纷,法律制度都被触发。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疫情下合同如何履行的问题,该问题也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热点,也是一个“民生点”。尤其是经过招投标程序的合同,疫情所造成合同履行情况与招投标时已发生变化,在此情况下,合同是否能够依据合同相对方真实意思表示而进行变更? 根据《招标投标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此条法律规定意为招标人和中标人之间签订的合同须以招投标文件为准,不得背离其招标过程中确定的实质性内容。实践中,经常会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客观情况的变化,此时需根据变化情况修改合同内容,例如发生不可抗力、情势变更、设计变更等与招标时有重大变化的情况。此时,根据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是否可以订立变更合同内容的协议,以合同内容或招投标文件中的内容为准确定招标投标法律关系下的约定内容则成为了值得探讨的问题。 根据《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57条规定:“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依照招标投标法和本条例的规定签订书面合同,合同的标的、价款、质量、履行期限等主要条款应当与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的内容一致。”也就是说,招标人与中标人所签订合同应该与招标文件、中标人的投标文件的主要内容一致。设定这样的法律规定原因在于,在招投标程序中,依据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根据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确立中标人之后,如果经过招投标程序的合同的签订还可以再违背招投标文件,则会损害其他未中标人、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甚至会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公共利益,也就是上述案件中法院认为可能存在的负面效果。因此,要求项目履行过程中的各种条件与招标文件一致,不得再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此出发点是《招标投标法》必然的要求,存在对招投标文件和签订合同内容一致性的要求也是合乎法律精神的。 但是,笔者认为我们应当要以探求真意为原则,通过确定招投标文件的约定内容为当事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确定应当以招投标文件为准,如果招标人与中标人更改招投标文件中的约定并非基于合理合法的原因,那么能够推导出的必然结论是双方是出于某些利益的考虑对之前已经确定的条件进行变更,由于不存在变更的法定理由,因此是不合法的变更,在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的语境下已经构成了对公共利益的损害。但是,如果招标人和中标人出于客观情况发生变化等法定的合同变更条件变更合同,则此时可以适用相关法律关于合同变更的有关条款,例如《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关于情势变更的规定,“合同成立后,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与对方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可以看出情势变更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合同因清偿而消灭之前,合同赖以订立的客观情势发生了当事人订立合同时不可预见的异常变动,导致合同的基础动摇或丧失,若继续维持合同原有效力有悖于诚实信用,将导致显失公平的后果,则应允许合同当事人通过司法程序变更合同内容或者解除合同的制度。根据上述案例来看,法院考量情势变更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属性,即无法预见的和不属于商业风险的。而情势变更,也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合同变更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对导致双方约定与实践不一致的合同应当进行具体分析,确定其背离招投标文件的原因,根据不同原因进行不同方式的处理。若法律规定在履行过程中合同不可以变更,必须与招投标文件的规定一致,那么实践中客观情况发生变化使得履行合同存在障碍时,后续的工作将无法进行,这显然与《招标投标法》的立法目的相悖,因此,此时适用《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的规定更加合理合法。 综上,当经过招投标程序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情势变更的情形,双方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变更合同条款,这种变更是合法的。与此相类似,例如发生不可抗力、设计变更、地质情况等与招标时有重大变化等其他合理合法情形下,双方当事人拥有变更合同条款的权利,而在依此变更后如果发生争议,也不应当依据《招标投标法》第四十六条认定合同无效。 |
经过招投标程序后签订的合同,在履行过程中是否可以进行变更?
时间:2021-09-24 18:14来源:五辰律所 作者:陈茜律师 点击: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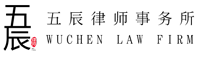

 五辰律师公众号
五辰律师公众号
 五辰律师抖音号
五辰律师抖音号
 五辰律师视频号
五辰律师视频号